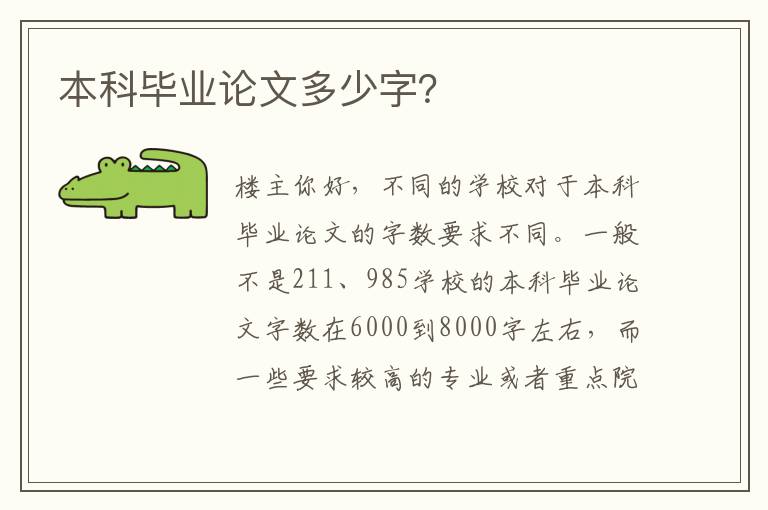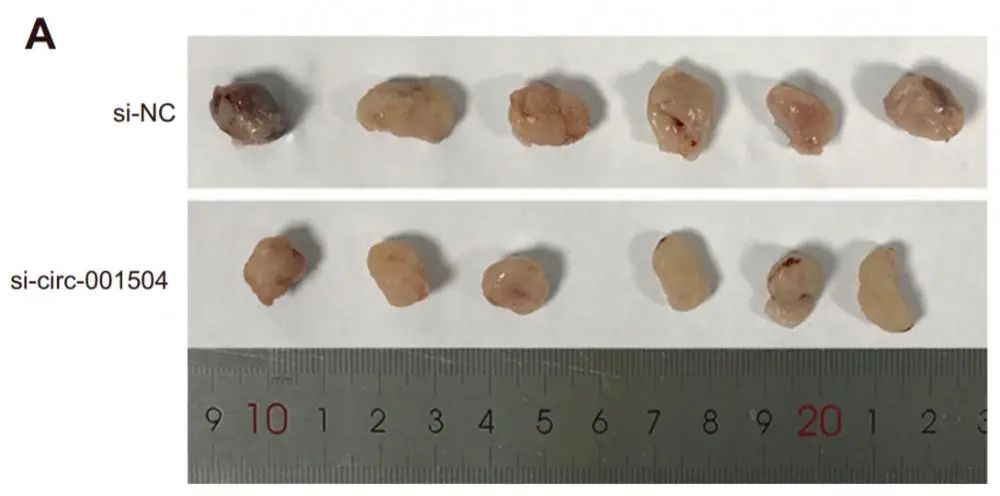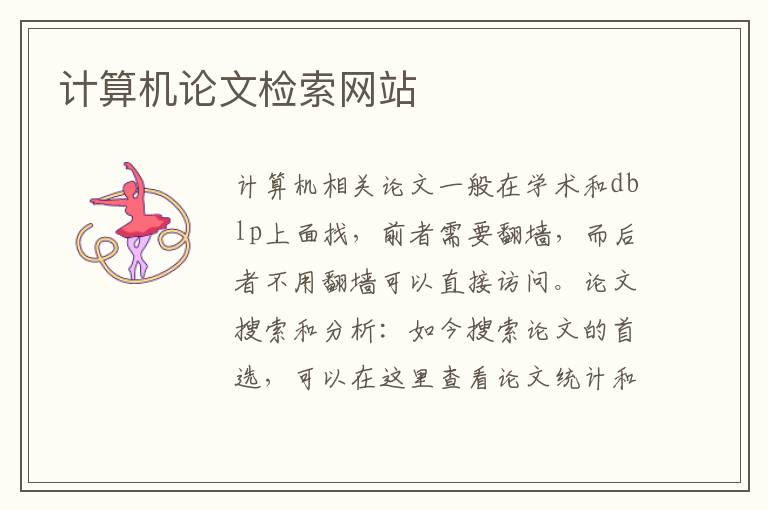從法學論文寫作中的命題缺失現象切入

作為問題的“問題意識”
——從法學論文寫作中的命題缺失現象切入
尤陳俊 |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5期
那種按照教科書式體例撰寫的法學論文,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有論域而無論題”,亦即只是選定了一個研究領域、對象或范圍進行面面俱到的介紹和敘述,卻沒有從中提煉出一個中心論題貫穿全文始終并加以論證。教科書式的寫作風格在今天仍然頑強乃至頑固地繼續影響著法學論文的寫作,這在很多題為“××制度研究”或“論××制度”的碩博士學位論文當中體現得尤其明顯。之所以仍然存在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是與對問題意識的重視不夠和認識誤區有關,特別是沒有充分意識到問題()、論題()和命題()之間的區別。對于如何提煉問題意識這一問題的思考,可以圍繞“書本知識VS.社會實踐”“歷史視野VS. 現實關懷”和“中國意識VS. 國際視野”這三組概念展開。
過去的20多年間(尤其是1999年開始的全國大學擴招以后),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作品生產均在規模上總體呈現出快速發展甚至急劇膨脹的趨勢。但在這種“繁榮”景象之下,卻時常可以聽到很多嘆息之聲。一方面,每年的春季學期,常常會有很多法學教師抱怨閱讀一些無甚學術新意的畢業論文并撰寫評閱意見實在是一種令人痛苦的折磨。另一方面,在國內各法律院系碩博士研究生每年通過答辯的兩三萬篇畢業論文,以及各種刊物上每年發表的數千篇法學論文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論文實際上很少受到同行們的關注,甚至有個別論文在收錄于中國知網數據庫并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后,還出現了“引用量為0、下載量也為0的現象”(這意味著連作者本人都懶得把自己的文章下載來看或加以保存)。
那些讓評閱老師們“怒其不爭”或為同行們所無視的所謂法學論文,之所以有如此命運,主要是與其學術質量不高乃至低下有關。而在導致其學術質量不高乃至低下的各種原因當中,除了有一些法學論文可能存在胡亂抄襲拼湊的學術不端外,很多法學論文本身缺乏“問題意識”是一個常見的共同點。因此,本文將以當代中國法學論文寫作為論域,將“問題意識”進行問題化處理之后,再漸次展開討論。
“有論域而無論題”的通病
在各校的法學研究生們每年生產出來的學位論文當中,有一類模式的論文題目相當常見,那就是“××制度研究”或“論××制度”。一些部門法研究領域,更是此類單調的模式化論文題目的重災區。此類題目不僅因幾乎千篇一律而欠缺文字表述方面的個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正文內容很多都缺乏一個貫穿始終的中心論題(更加不用說論題在學術上的創新性),而只是將與某種法律制度或法律現象有關的方方面面知識點都加以介紹、梳理和敘述,亦即“大都是按照題目對相關方面所做的‘知識性’的描述,而根本不是以某個理論問題而勾連起來的思考”。用一位學者的俏皮話來說,“結果,別人寫議論文,他寫成說明文了”!

稍稍翻閱這些論文,便不難發現其中有很多都屬于“有知識(介紹)而無(個人)見識”,在寫作框架上幾乎與教科書無異,以至于題目是“××制度研究”或“論××制度”,但其內容實際上變成了“××制度說明”或“××制度介紹”。這種按照教科書式體例寫就的論文,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有論域而無論題”,亦即只是選定了一個研究領域、對象或范圍,卻沒有從中提煉出一個貫穿全文始終的論題并圍繞其加以論述。例如,一篇題為“私募股權投資中的對賭協議研究”的法學碩士學位論文,其行文結構是“對私募股權投資中對賭協議的相關概念、本質、價值、運作機制及適用中的法律障礙等問題做一個分析”,就屬于上述所說的這種情況。在中國知網中所收錄的各校法學專業碩博士學位論文當中,存在此種情況的論文相當常見。
問題()、論題()和命題()的聯系與區別
這種教科書式寫作體例之所以在當下的法學論文(尤其是學位論文)中仍然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是與長期以來對問題意識的重視不夠和認識誤區有關。這種認識誤區的表現主要包括如下兩方面:其一,誤將“選題”等同于“問題意識”;其二,誤將教科書以及一些著作所體現的“體系意識”等同于“問題意識”。
多年前,一位曾在耶魯法學院求學的學者曾專門撰文介紹道,“法學博士論文應該有‘命題’在西方是一項普遍性的要求”,“它應該是貫穿整個博士論文的中心論點,是你試圖在論文中探討或論證的一個基本問題( )或基本觀點( )”,且一篇論文的中心命題只能是一個,并強調說,“論文的命題即是研究的出發點,也是研究的終結點”。 西方(尤其是美國)學界在學術訓練中這種對“命題”之不可或缺性的強調,與其建立在對、和這三個概念加以區分之基礎上的“問題意識”的極度重視有關。、和這三個英語單詞,雖然看起來似乎都可譯為“問題”,但其實存在著微妙的差別。仔細琢磨其各自的內涵,可將譯為“問題”,將譯為“話題”,而將譯為“命題”或者“論題”。在美國的學術界中,這種須從擬解答的問題中提煉出一以貫之的中心論題()并圍繞其展開論證的要求,并非僅適用于學位論文()的撰寫,而幾乎是所有學術刊物對論文()所設定的固定格式。
而中國法學院系的很多教師在指導學生撰寫論文時,通常是將主要的精力放在“選題”方面。不少法學教師對學生如何選題的指導,實際上還只是停留在問題()或話題()的層面,基本上都是從應當如何確定論文題目的大小(通常都青睞“小題大做”)、論文題目中所應有的主要知識點在寫作提綱中有無大的遺漏等方面著眼,而往往未能提升至命題()的層面對學生加以訓練。例如,一位前輩學者在1990年發表了一篇談如何撰寫民法論文的文章,其中以撰寫法人制度的論文作為例子談論文定題,并根據所涉問題的大小,分級列舉了一些論文題目作為參考,亦即“一級,如論法人制度的歷史發展、論我國法人制度等;二級,如論企業法人制度、論財團法人制度等;三級,如企業法人成立的條件、企業法人民事責任的承擔等;四級,如論企業法人章程、企業法人工作人員的民事責任等”。另一位前輩學者出版了一本講法學學位論文寫作的小冊子,在學生當中很受歡迎。該書專列了一章談學位論文的選題,其中列舉了一些其認為較好的博士論文題目設計,均是“××問題研究”之類的題目。
上述兩位學者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但坦率地說,就他們所推舉的那些論文題目而言,其實只是道出了擬研究的問題或話題,或者說只是提示了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此類題目的論文,雖然不排除其正文當中實際上也存在一個一以貫之的命題的可能性,但往往有更大的可能性是全篇以教科書式的體例面面俱到地鋪陳展開,亦即實際上是基于教科書所注重的“體系意識”而非論文更應注重的“問題意識”進行寫作。

這種“有論域而無(貫穿全文的)論題”的寫作風格,并非僅見于一些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在一些所謂學術專著當中亦時可看到。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很多學術專著不過是主題較窄的教科書”。不少此類題目的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和學術專著,雖然大致存在知識體系完備性方面的差別,但均缺乏一個貫穿全文的命題。這種現象,與上述那種主要注重如何劃定研究對象或范圍的選題習慣有很大關系。而那種選題習慣之所以仍然頑強乃至頑固地延續至今,又與改革開放以降的前幾十年里(這是中國法學恢復和重建的時期)中國法學研究的特點之一——“教科書法學”的寫作風格流行,烙在此時期成長起來的很多研究者身上的思維印記有關:“教科書通過教學,培育了未來的教師和學者,也因此既奠定了這些潛在的法學作者的思想圖式,也灌輸了其寫作方式。”
一些更年輕的中國法學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上述弊端,轉而強調法學研究應當要有真正的問題意識。尤其是就法學論文寫作而言,最關鍵的在于如何發現、提煉和論證一個有學術創新性的命題,而并非只是劃定了一片大致的研究范圍進行缺乏中心命題的體系化敘述。陳瑞華舉過一些貌似面面俱到但實則缺乏問題意識的“教科書式寫作體例”的論文作為反面例子,“比如一篇有關民事侵權問題的博士論文,體例上包括侵權的概念、歷史發展、兩大法系侵權法的比較、有關發展動向、中國侵權法的問題和侵權立法的現狀、未來侵權法立法的若干設想等部分”。何海波也指出,一些學生仿照教科書中某章某節的標題擬定自己論文的題目(例如“論締約過失”、“行政檢查研究”),卻沒有意識到在實踐中或理論上究竟存在什么問題,以至于寫出來的文章“既沒有重點也沒有結論,既不要堅持什么也不反對什么,既不和人家商榷也沒準備被人家質疑”。對于何海波所批評的這種寫法,姚建宗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由于不少研究者錯誤地“把自己的研究‘領域’或研究‘范圍’當做自己所研究的‘問題’”。
如今,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法學研究者在自己寫作時注重對問題、話題和命題的區分,意識到問題意識對于一篇論文的重要性。舉我自己幾年前撰寫的一篇小文章為例。我的那篇文章,從幾乎任何一本《中國法制史》教材均會提及的“秦代是以身高來作為是否要承擔刑事責任的標準”入手,對“秦代為何是以身高而非年齡作為刑事責任能力之分類標準”這一問題加以追問,通過考察秦漢時期國家認證能力的變化這一話題,最終證立了一個命題,亦即認為秦代論處刑責時以身高為準,而漢代以來則改以年齡而斷這種發生在刑事法制領域內的變化,是從先秦至秦漢時期國家在“基礎性權力”方面得到提升所帶來的一個結果。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青年法學教師在指導學生撰寫論文時,也更加注重引導學生們首先須基于問題意識提煉出一個命題,而不是讓其選定了一個問題之后便開始方方面面鋪陳開來寫作。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變化是,之前相當常見的那種“××制度研究”或“論××制度”的學位論文選題,如今在很多青年法學教師那里已很難獲得通過,故而此類題目的論文數量也相對有所減少。
問題意識從哪里來
真正的問題意識,乃是建立在對問題、話題和命題之聯系和區別有明確意識的基礎之上。所謂“問題意識”,用一位學者所做的精煉概括來說,是指“作者必須發現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從中提煉出一個學術上的話題(),然后給出自己的命題()并加以論證”。那么,這種問題意識具體可以從何處提煉?
(一)書本知識VS.社會實踐
問題意識既可以來自對書本當中的某一知識譜系的梳理、總結和反思,也可以來自社會實踐中遇到的一些現實困惑所帶來的智識觸動。
前述提及的那篇拙文,通過分析秦代在論處刑責時以身高為準而漢代以來則改以年齡而斷這種變化的背后原因,揭示了其所反映的乃是從先秦至秦漢時期國家在認證能力上有著一個重大的飛躍,這種問題意識便主要是來自閱讀相關歷史文獻后結合相關理論的思考。此類主要由對某一知識譜系重加審視而生發出來的問題意識,在法學研究中多見于一些重思辨或偏考證的領域,例如法哲學、法制史、法律思想史以及法學學術史等領域的研究,常常體現為一種書齋中的學問。
與之相對,另一類問題意識則主要來自社會實踐中(親身體驗或調研所得)一些現象所帶來的觸動與刺激。例如陳柏峰的一篇研究基層社會的彈性執法(此即“話題”)的論文,其問題意識便是源自他于2007年4月至2014年7月間,在湖北省某市多次對禁止非法機動三輪車的執法情況進行調研時所發現的執法不嚴現象(此即“問題”),通過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彈性執法發生在中國法治的特定實踐中,有著轉型期獨特的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背景,即客觀存在的社會群體利益矛盾、尚難容納多元利益訴求的法律系統、執法對象激發的社會話語壓力、青睞變通權宜的法律文化四者之間的張力與合力”這一命題,并進一步將之提升至執法能力與國家治理能力之關聯的理論高度予以延伸闡發。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第二類問題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借助于相關學術理論的印照,不然往往便會淪為對社會現象的簡單描述和展示(就像一些調查報告那樣),而無法從“問題”中提煉出具有學術意義的“命題”。例如,蘇力從一起拼湊但不是虛假的強奸“私了”案件入手,討論了“法律規避”這一理論性話題,并進而論證了“法律規避是制度創新的一種途徑”這一富有學術沖擊力(同時也具有學術爭議性)的命題。這種討論深度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他對于西方學術界的法律多元理論的知識儲備和熟練運用。只不過相對于那種主要由對某一知識譜系重加審視而生發出來的問題意識而言,此類問題意識首先是由社會實踐而非書齋中的單純玄思所激發。這種情況,在那些立基于經驗研究的法社會學研究論著中相當常見。
有學者將論文的選題分為理論性的選題和實踐性的選題兩大類。在我看來,即便是實踐性的選題或應用型的法學論文,也應當有一個貫穿全文的“命題”,而不能寫成面面俱到的法律實務操作指南。只不過相